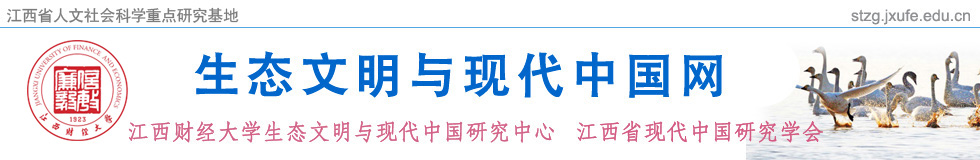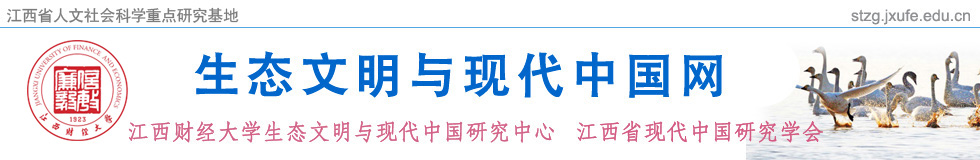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4-19(6)
不可忽视的是,费希特比黑格尔更为冷静地意识到,现代社会不是自然和谐的状态,而是一种政治工作的结果。
例如费希特在1794年的就职演讲中就对专业化的职业分工的要求做了反思。如果这种专业化不是一个强制性规整指派的结果,而是基于一种自由的职业选择,那么面向自由的教育就成为自由选择所必须依赖的一个本质性前提。这反过来又预设每个人都必定已然如此:不仅同他人分享相应于他天分和能力的东西,同时也从他人那里“接受”自己本来并不能获得的东西。据此,教育是一个由相互交换构成的高要求的社会化过程。其结果是产生了那种为某个自由决定奠定基础的自由“平等”。费希特补充说,对这样一种决定,社会无论如何都有权要求对它的应用。法国大革命后,这些观点对于德国的封建社会而言是革命性的,又与一种广义的教育概念相连。
黑格尔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坚持说,“从出于权威的意见与出于自身论证的意见”的翻转是不够的,因为自身的证明是否真实,还要通过抛弃外在法令来非必然地保障。同在费希特那里一样,教育承载颇重,并且处在资产阶级替换或将替换贵族统治这一事实逐渐被意识到的时代。现在必须反思,在何种状况下,自身意见的表达不仅是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服务于所谓“自由”的东西。
此后关于所谓有教养的中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的说法具有特别的消极色彩。有教养的市民(Bildungsbürger)从尼采关于有教养的市侩(Bildungsphilister)的说法开始,便与“古典主义者”的任务一道被锁进了书橱。如在黑格尔那里所看到的,教育与资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连接,正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对立。教育是通向政治参与的道路。因此就其本来意思而言,它是意识自身的工作,并因此达到一个持续经验的过程,促使个体从它所信任的以及对它而言显得确定的东西中走出来,去面对那些不寻常的视角和期望。黑格尔甚至将“教育以及其现实性的领域”描述为“精神的自我异化的世界”。异化在黑格尔看来也是一个否定的东西,是某物本身不应当是的东西。但他同样坚信,我们只有通过异化、外化的否定性经验才能学会把握自由和任意之间的差别。
由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教育这个概念存在着怎样的潜力:一种与功用最大化的技术性视角不相干的潜力,它的目的内在于自身,同时又以一种广义的实践为目标。
这就将耶拿当时的状况与当代对大学改革的探讨关联起来。当时也涉及大学改革的主题。因为如果按照这种新的教育概念,那么当时的大学体系就不能像早先那样存在了。谁将教育理解为面向自由的教育,就不会愿意让学生领走一个预先布置好的文献表以获得泛泛了解,就不会不强调学生自己的判断力,让他们被迫死记硬背;他自己也不可能有兴趣接手一本引进的教科书,逐字逐句照本宣科,并遵照几条指引评注他所宣读的东西。然而直到1800年前后,这正是通行的大学课堂实践方式。就是康德在哥尼斯堡也仍然承担着以这种方式讲授的课程,由此可以衡量,当时在耶拿上演了怎样一场大学革命。
费希特并不照本宣科,而是向他的听众提出自己的思想,接着逐渐将它印刷出来。他讨厌按照条条框框的迂腐要求反复地使用同样一些概念,以使人们能更好地记住它们。费希特想塑造的是那种独立思考并具有批判能力的学习者,因此有意识地变换他的概念用法。他想避免这种情况,即一个观点不是得自周全的思考,而只是因为被重复,如同那在考试中重复出现的令人讨厌的内容。
以这种并不轻松,而是紧张的、面向自由的教育为标志的大学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威廉・洪堡基于其在耶拿的经验,在柏林进行了著名的“洪堡的大学改革”。教授者和学习者不应再像之前那样瞻顾知识的实际用途,也不像在中学里那样追求“完成了的知识”,而是共同献身于一种永不完结的科学。洪堡还告诫说,不许干涉和阻挠这种共同的、以真正的兴趣为中心的研究和教学活动。
这里说的不是一种远离所有生活需求的、纯粹科学的象牙塔。正是因为国家以及人性“涉及的不是知识和言论,而是品性和行为”,所以洪堡认为,如果大学是一个允许努力自由思考和独立思考的地方,那么它将最好地服务于国家和人性这个目标。
(作者:德国波鸿大学哲学系 Birgit Sandkaulen 谢永康/译)